我爱上维吾尔族女学生,她父母反对我们在一起,还要与女儿断绝关系
张爱玲曾说:“因为一个人,爱上一座城。”
因为她,我爱上了新疆,爱上了维吾尔这个民族。
因为她,在这些年里,我坐着绿皮火车,踏遍了新疆的每一个角落,试图访遍与新疆相关的整个西域世界,走遍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和西亚国家。
最后,我的爱情,也永远埋葬在了新疆这块遥远而孤独的土地上。

(在新疆独自旅行)
我叫文枫,1995年出生于长江边的一个江南小城。我是家中独生子,爸爸一年到头在外忙于生意,妈妈在成人大学做辅导员,工作也很忙。
一家五口人挤在外公家六七十平米的房子里,我和外公外婆共住一个房间。也许是从小没有独立的私人空间,所以长大后,我才会钟爱新疆那种大气壮阔的风景。
妈妈很喜欢读书,在她的耳濡目染下,我从小就喜爱读书,也非常喜欢写作,曾拿过全国文学大赛的金奖。但阴差阳错的是,我却走了十多年的理科道路。
初中时,我被选入市计算机编程实验班,学习C语言编程。参加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,还拿到了二等奖,如愿考进了省重点高中的理科实验班。
虽然进了实验班,但我在理科方面的天赋并不高,始终对数理化不感兴趣。结果,高考是我学生生涯中考得最差的一次,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。

(初中时期)
人争一口气,佛争一炷香。为一雪前耻,从进入大学开始,我就准备考研。当时,我的考研目标是复旦大学的金融系。之所以选择复旦大学,除了自己咽不下这口气外,我还想为外公和母亲争回一次脸面。
外公原是地道的上海人,后知青下乡,户口也被迁出上海,从那以后,外公就再也没有机会迁回上海。母亲每年回上海探亲,那边的兄弟姐妹都会称母亲为“乡下人”,这种带有歧视的称呼让母亲很屈辱。
因此,我想重回上海,为母亲争一口气。
可惜,天不遂人愿,考了整整两年,都没考上。直到第三年,我换了一个目标,最终考上了北京另一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。
毕业后,我凭着学校的名气和自身的努力,进入北京的央企工作,也拿到了北京户口。虽然不是我熟悉的上海,但单位毕竟直属中央,是一个大平台,心里的执念才慢慢释怀。

(研究生毕业照)
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,而旅行,是世间最好的治愈良药。我的旅行围绕新疆,始于两段刻骨铭心的感情。
10年前,就读大一的我,曾被一位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吸引。
她叫麦迪娜(化名),是我的大学同学。和迪丽热巴一样,她拥有清澈的大眼睛,高翘的鼻梁,深邃的眼窝,扑闪的长睫毛,圆润的下巴。精致立体的五官无一不长在我的审美点上。她的温柔善良,善解人意,总是让我感到温暖和美好。
学校里,我们经常一起吃饭,一起上课,一起看书,一起去清真寺,一起听她们民族的维吾尔语流行歌曲。
那些年,因新疆暴恐事件,维吾尔族的声誉受到了很大影响。一些维吾尔族大学毕业生在内地找工作时被拒,住酒店时被拒,过安检时被扣留。但是,在我眼中,麦迪娜是一个有教养和文化的大学生,更是一个纯洁的天使。

(第六次去新疆,在伊犁河畔)
然而,面对与我的感情,麦迪娜却进退两难。她来自新疆喀什的农村,在我们上大学的那些年,南疆很多地区,尤其是农村的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,因宗教信仰和一些其他原因,当时很多维吾尔族人不与汉族人通婚。
来内地上大学前,她的父母就要求她远离汉族男生。所以她一直是瞒着父母和我交往,但心里又很矛盾,感觉对不起她的父母。
纸终究包不住火,我们的地下恋情还是被她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发现,果不其然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。为了取得她父母的认可,也为了能继续和她在一起,我对她说我愿意为了她加入她们的宗教信仰。
可是,一切都是徒劳的。如果她坚持和我在一起,她的父母就要和她断绝亲情关系。即使我改变宗教信仰,他们依旧不能接受一个有着汉族血统的男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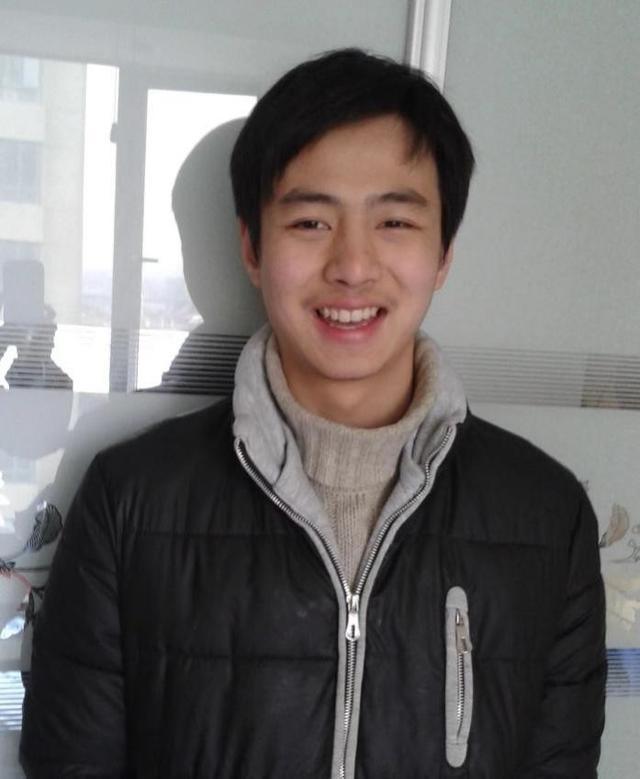
(大一时候的我)
在民族和宗教信仰这些宏大的问题面前,我们两个刚满18岁的少男少女脆弱而稚嫩的感情,如同一片薄冰,一触即碎。
因为她,我爱上了新疆,爱上了维吾尔族这个民族,但他们却没法接纳我,这对刚满18岁的我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打击。
这段感情虽然维持不到一年,却影响了我整整十年。后来的十次新疆之旅,就是我对她爱屋及乌的见证。
谈恋爱时,她经常给我介绍维吾尔族的音乐文化,还有与维吾尔族的语言文化相近的一些中亚国家,让我对西域这片土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一直想去看看。和她分手很多年后的2018年,我终于有机会踏上这片土地。
那是在大学毕业后,我考研失败,被调剂到新疆财经大学参加研究生复试。
分手这么多年,我第一次来到麦迪娜的家乡——新疆。

(分手多年之后,终于来到新疆)
多年过去,我们都已成熟,当初青涩的感情现在已转化为友谊。她已在老家的县城工作,已有男友,不方便与我见面。而恰好,她的闺蜜在市区,于是请她的闺蜜接待了我。
她的闺蜜叫阿依努尔(化名),虽然以前我们都在同一所大学,但不曾认识。和麦迪娜一样,阿依努尔也有着惊为天人的美貌。
那是一个将世界各国美女优点集于一身的混血美女,脸型像法国人,尖尖的鼻子像希腊人,长长的睫毛和白皙的皮肤像俄罗斯人,深深的眼窝和蓝色的眼睛像波斯人。
麦迪娜黑发黑瞳,长得更像西亚人;而阿依努尔则是棕色头发棕色眼睛,长得更像欧洲人。
对待远方来的客人,维吾尔族人都会热情而有礼地款待,阿依努尔也不例外。她在喀什的一家高档的土耳其餐厅招待了我。

(坐在维吾尔地毯上)
席间,我们彼此都很意外地发现,我俩聊得很投缘,像认识了很久的老友,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
随后,我和阿依努尔一起坐车回到喀什,她邀请我去她租住的房子做客。那次,她特地从房里拿出一张垫子放在客厅的地毯上,让我坐在上面。
据说这是他们待客的最高礼节,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。
然而,更让我惊讶的是,她对我说道:“要是大学时我们俩就认识了,你会不会喜欢上我?”当时,我心弦一颤,心跳倏地慢了半拍。在这暧昧的气氛中,我还是努力克制了自己。
也许,经过两天的相处,在我和阿依努尔之间,微妙的情愫已经悄然萌芽了。
在后来的日子中,我经常会在火车上听着感伤的维吾尔语情歌,想起阿依努尔意味深长的眼神,和她的那句撩动我心弦的问话。
回内地后不久,阿依努尔就出嫁了。我们终究只是萍水之缘。

(第二次去新疆,在帕米尔高原)
第二年,我考上了北京的研究生。入学前夕,我第二次去了新疆,打算深入探索这片梦幻瑰丽的土地。这里热烈的异域风情和雄浑苍凉的美景,正是我魂牵梦萦的“诗和远方”。
对于我的再次到来,阿依努尔很意外。这次,她像认识多年的老友一样,热情地邀请我去天山脚下的老家做客。
那是我第一次踏入一个传统维吾尔族人的家中,几乎和网络上看到的维吾尔族的生活一模一样,满桌子的瓜果和馕,家里的地板上铺满了地毯,到处都是华丽的装饰。
晚餐,她的父母用维吾尔族家常的“羊肉抓饭”招待了我。她的整个家族几乎都来了,围坐在客厅的地毯上,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。有些年长的人不会说汉语,阿依努尔就在我们之间做着翻译。
饭后,阿依努尔告诉我,她的婚姻并不幸福,法院的离婚判决已经下了,正等着领离婚证。

(伊人已去,往事如烟)
接着,她好似自言自语地说,上大学时,她一直很羡慕我对前女友的深情,也很欣赏我可以为了爱而不顾一切的性格。她也曾幻想过,要是她也能有这样一个男孩,这样炽热而勇敢地对她,该多么美好。
想到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,我在片刻的犹豫之后,向她说出了自己的情愫,不想给自己再留遗憾。一开口,才发现几乎像是在表白。她颇感意外,但随即,也发现了自己对我的好感。
只是,她已在新疆做了公务员。作为一个维吾尔族人,辞职去北京找工作难度很大。而且,她也不可能离开养育她的父母,与我私奔到千里之外的北京。
虽然她也心动了,但纠结之下,还是温柔地拒绝了我。她说,她刚结束一段失败的婚姻,有些筋疲力尽,暂时没有力气去回应一份新的感情。
之后,我们又经历了几多波折。但最终,还是失散于人海。
多年过去,我已不再有年少时义无反顾的勇气,再去开启一段轰轰烈烈、却又伤人伤己的感情。

(再回首,恍然如梦)
我把回忆珍藏在心底,背上心爱的吉他,一路流浪,把自己放逐在遥远而又孤独的西域大地上。
把我的回忆,葬在这大漠戈壁;
让我的故事,沉睡在这茫茫荒野;
任我的思念,飘散在这呼啸而过的大风中。
此后的几年中,我去了8次新疆,走遍了新疆的每一条铁路线。沿着南疆铁路,我环绕过整个塔里木盆地;沿着和若铁路,我横穿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;沿着北疆的铁路,我穿越天山,进入温柔如梦的伊犁河谷。
就这样,坐着复古的绿皮火车,我游遍了新疆的每一个角落。
从北疆的阿勒泰、克拉玛依、伊犁到东疆的吐鲁番、哈密,再到南疆的喀什、和田、阿克苏和库尔勒,甚至去了多年前还无人问津的莎车、疏勒、库车、泽普、伽师、若羌、托克逊、鄯善……
夕阳下,总有一个孤独的背影,在金碧辉煌的西域荒原上,独自游荡……

(我独自走在荒原上,一身苍凉)
十年后的今天,新疆的社会风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人们的思想逐渐开放,维吾尔族和汉族谈恋爱、通婚的情况越来越多。有的地方还会给结婚的维吾尔族和汉族夫妻以物质奖励,比如在乌鲁木齐,听说奖励能达到十多万,有的甚至还给房子。
当我听到这些,不禁想起,如果我和麦迪娜晚生十年,我们的感情不会遇到十年前的那些来自外部的阻力,我们的人生会不会就此改变……
在后来的几年中,我继续追随着维吾尔族的历史和文化轨迹,从新疆继续往西走出中国的边界,进入更西的“西域”——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、哈萨克斯坦,西亚的土耳其、阿塞拜疆等国家。这些国家的文化和语言都和维吾尔族相近,说的语言都同属"突厥语"。
我从新疆的陆路口岸出境,从中国最西端,一路走到了亚洲最西端,近乎穿越了一次丝绸之路。

(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)
在人种和基因上,和维吾尔人最接近的是乌兹别克人。
上大学时,麦迪娜就告诉我,学校有两个乌兹别克族学姐。如果在大街上碰到这两个民族的人,他们自己都很难分辨。
地理上,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只隔着一座天山。维吾尔语和乌兹别克语非常相似,就好像汉族的两种汉语方言。
因为语言互通,很多维吾尔族人都喜欢听乌兹别克斯坦的流行歌曲。麦迪娜也经常带着我一起听,歌词她都能听懂。虽然我听不懂,但我很快就爱上了。
我跟着麦迪娜听遍了土耳其、哈萨克、阿塞拜疆等几乎所有突厥语国家的流行歌曲,其中乌兹别克的是我听过的最温柔、最深情的,还带着浓厚的俄罗斯式的忧伤。
即使在分手后十年的现在,我也经常听乌兹别克斯坦的歌曲。
爱屋及乌,我一直想去这个国家看看,有着这么温柔的音乐,让我初恋魂牵梦萦的地方,到底是什么样子?

(我身后的是乌兹别克人,剩下的都是哈萨克人)
于是,我从新疆坐着火车出国,越过高大巍峨的天山,进入了古老的西域深处,来到了天山另一端的乌兹别克斯坦。
因一个人,来到这片遥远的异域,而那个人却早已不在身边。我仿佛一个寻家的浪子,漫无目的地游荡。
夜幕降临,人们在篝火晚会上欢聚一堂。火焰燃烧着木材,也燃烧着人们的热情。
帐篷的主人邀请我们跳舞,伴着熟悉的乌兹别克音乐,我试着跳起了麦迪娜教过我的维吾尔舞蹈,这让在座的乌兹别克人大吃一惊。
因为我长着一张东亚面孔,却跳着中亚的西域舞蹈。
当我打开手机,播放出维吾尔族的流行歌曲,他们更震惊了。因为这些歌曲的歌词他们都听得懂,却又不像是他们国家的音乐。我告诉他们,这是中国的歌曲,是维吾尔人的音乐。

(左边是哈萨克人,右边是乌兹别克人)
在认识麦迪娜之后,我就对维吾尔族的长相差异之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她们有的人很像外国人,有的人却又和汉族人没什么两样。
就像一个朋友,她的父母都是纯正的维吾尔族。她的母亲完全是亚洲人的长相,但父亲长得像德国人,妹妹80%像俄罗斯人,而她本人有50%像法国人。同一个民族,一家人,却有着不同的长相,不得不让人感到神奇。
北疆在古代与汉人的中原地区交流更多,有很多汉人,那里的维吾尔族也长得更像汉族。南疆的维吾尔族则有更多的混血基因,很多长得很像欧洲人。
在喀什,曾见过一个维族男生,蓝色的眼睛,金黄色的头发,眉眼和《泰坦尼克号》里的男主莱昂纳多几乎一模一样。

(像不像维吾尔族人?)
最后,再说一个在伊朗背包旅行时遇到的趣事。那天,我在伊斯法罕的广场上一个人游荡,遇到一对伊朗男女,邀请我一起喝茶聊天。男人头发花白,长相英俊,风度翩翩,会说一些简单的英语,是伊朗某国企的CEO,即将退休了。女人看起来年轻很多,是一位医学博士。
聊天时,我注意到他们举止亲密,心中猜想他们不是夫妻,就是兄妹或父女。结果,大叔告诉我,他们是情人。更炸裂的是,这个女人竟然是大叔儿子的妻子,也就是大叔的儿媳!
这个女人说她狂热地爱着这位年近花甲的大叔。当时嫁给他儿子,也是为了能一辈子接近他。更震惊的是,她丈夫知道真相后,居然接受了。女人说,如果当初丈夫不接受,她随时准备好了“为爱殉情”。
我以为,这种三观炸裂的故事一般只会出现在电影或小说中,没想到在伊朗却看似很平常。这位大叔淡然地告诉我:“在伊朗,男人有1个妻子,10个女朋友。”

(伊朗的特殊情侣)
十年之旅,我以爱之名,以新疆为界,用脚步丈量着神秘的西域。
有些人注定不属于自己,但遇到了也是一种幸运。如果没有她,我不会如同带着使命一般,一次又一次地跨越几千公里前往遥远的西域,踏上神秘的丝绸之路。在新疆的几乎每个城市,都留下了无数的回忆与故事。
其实,生命中的每段经历,都是老天的馈赠。不论是快乐还是痛苦,都是宝贵的财富。就如同我的初恋,充满了无奈与悲凉。即使十年过去,仍然能记得当初,对个人在社会大背景下的渺小的无奈。但,现在回头看,我不后悔。爱过,就没有遗憾。
十年间,经历了刻骨铭心的“异族恋”,到后来开始背包旅行,沿着丝绸之路,游遍新疆和西域的中西亚国家,正是我青年时代梦想中的“诗和远方”。再回首,却如同大梦一场。
